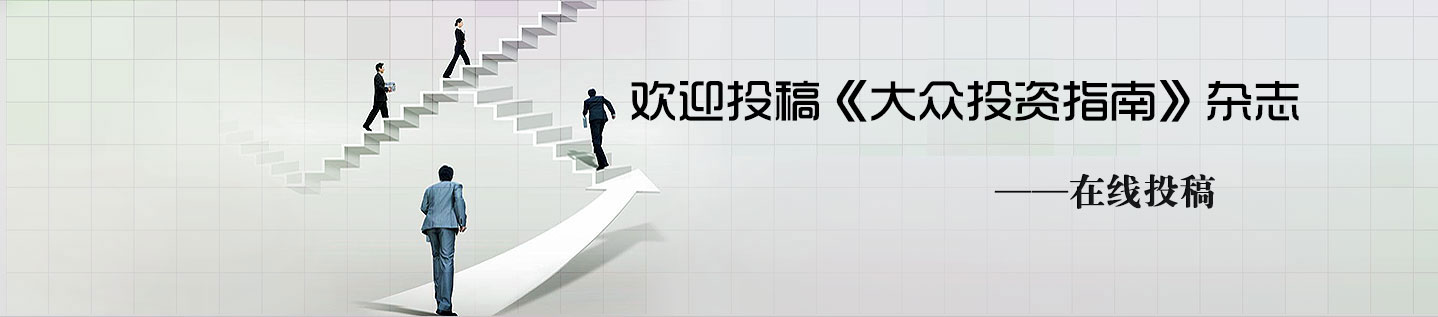摘要:与以往从静态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不同,转而从动态修复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对合规成本及其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审计费用的显著增加相比,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并未显著引起企业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控建设更倾向于“监管需求”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往往会导致高管的变更,而高管变更则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并且这一结果在政府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的环境下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内部控制建设并未真正成为企业的“自律”行为,仍然需要强化外部审计与政府内控监管,另一方面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压力传递价值,有助于企业优化高管团队,强化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改进公司治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合规成本;高管变更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意味着企业面临潜在的风险,而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无疑会降低利益相关者与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使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及可靠性、甚至对公司的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怀疑,由此造成一些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不愿意及时报告缺陷信息(Rice和Weber,2012)[1]。而政府监管部门则通过强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督促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以防范和降低各类风险,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利益。当面临政府监管时,企业可能采用“形式合规”和“实质有效”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是否会对下一期的企业合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合规成本的付出是“形式合规”还是“实质有效”?
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针对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中发现的重大缺陷提出整改措施,并在下一年度的内控评价报告中对前期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否完成整改以及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情况作出报告。然而,这一行为受到企业高管层的重要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组织行为及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反映(Hambrick等,1984)[2],企业高管及其权力配置会影响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效率(程小可等,2013)[3]。然而,在新兴加转轨的经济背景下,公司高管为了攫取控制权利益,会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导致内部控制的装饰性功能远远强于制度的约束性功能,这在高管权力集中的情景下表现得更为充分(Hambrick等,2007)[4]。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是否会导致高管的变更?高管变更之后是否意味着管理层的权力配置朝着有助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政府对内部控制监管力度的不断强化,是否更加有助于高管变化及其权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对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作用。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08—2014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内部控制缺陷—合规成本—高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逻辑链条,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对上市公司合规成本和高管变更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高管变更是否有助于上市公司后续年份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揭示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对合规成本及其高管接替风险的作用机理。本文通过缺陷修复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高管变更及其政府监管如何作用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机理,既甄别了中国企业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投入资源和改善公司治理来改善内部控制达到“实质有效”的需求,拓展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经济后果的有关文献,也展示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管控系统的基本功能与免疫自稳能力,这对于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改进具有强有力的实践指导价值。第二,构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静态与动态结合、内部与外部互动的治理机制框架。本文不是简单地继承以往从静态的视角、内部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导致合规成本增加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从缺陷修复的动态视角、外部治理改进和政府监管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高管变更进而对公司治理、政府监管之间的互动作用,为内部控制风险免疫环境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合规成本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监管实施将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合规成本,包括内部控制建设与信息披露成本、治理成本、审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国外已有文献发现,尽管遵循404条款带来的遵循成本相当高昂,但企业会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如积极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聘任更具专业经历或者资质的高管或者CFO等(Li等,2010;Johnstone等,2011)[5] [6],又如企业通过持续投入资源来改善内部控制(Hall和Gaetanos,2006)[7]。但也有研究发现由于遵循SOX 法案增加了公司的披露成本,很多公司选择从美国退市(Leuz等,2008)[8]。中国证监会2007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发布整改计划,并且披露整改效果报告。那么,企业遵循成本(整改内部控制缺陷投入的资源)的发生是企业实质性的自我完善和持续改进的体现——“实质有效”还是仅仅为了迎合监管的要求——“形式合规”?
1. 合规成本的影响。在外界压力和内在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公司治理层与管理层将通过自查并调动企业内部资源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整改,以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着力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为此,企业将为之付出大量直接的合规成本,如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对企业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估与改进、在已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基础上改进和完善内控环境体系、重新梳理并完善相关业务流程、重新评估风险、补充和修改相应的管控制度、升级信息系统等,由此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也即本文所称的合规成本,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后文简称“销管费用”)。陈骏(2014)[9]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上市公司在内控监管实施前后内控遵循成本的变化,其研究结果表明,内控强制监管确实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遵循成本,但该成本仅体现在规则执行的首年度。Ahmed等(2010)[10]发现SOX法案导致企业营业成本显著上升,营业利润显著下降,尤其对于規模较小、业务复杂度更高和成长性较低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Alexander等(2013)[11]研究发现,遵循SOX法案404条款发生的成本支出显著高于带来的收益,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小、正处于成长期的公司成本支出更为巨大。因此,预期内控缺陷的披露将导致上述企业为满足监管要求、遵循内部控制规范、修复已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而增加直接成本的支出。
2. 审计费用的影响。Ashbaugh等(2009)[12]通过对经过SOX-404审计的和未经过审计的公司的比较,在控制了其他风险因素后,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有显著较高的特殊风险。审计风险越高,根据审计师的风险偏好,要么不接受审计聘约,要么要求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Raghunandan和Rama(2006)、Hogan和Wilkins(2008)[13] [14]研究认为,对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审计师将会收取风险溢价以应对可能的诉讼风险,同时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的成本。Hoitash等(2008)[15]研究表明,风险定价是审计收费一个重点内容,事务所对审计业务风险较高的公司提高收費,以此补偿增加的诉讼保险费用。Raghunandan和Rama(2006)[13]的研究表明,与无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企业相比,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企业的审计费用较高;张敏、朱小平(2010)[16]以2008年沪市和深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如果存在内部控制问题会对审计定价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李越冬等(2014)[17]发现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间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即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Kinney和Shepardson(2011)[18]以审计费用的增加额作为改进内控监管增量成本的替代变量,考察SOX法案实施过程中不同内部控制的遵循成本,结果发现预期内控缺陷的披露将导致额外的审计费用。按照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严重程度,内部控制缺陷分为重大缺陷(也称实质性漏洞)、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反映了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的高低,内控缺陷越严重,企业偏离控制目标越远,越有可能导致内部控制无效。因此,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的一个负向维度指标,必然是审计师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提高审计效率与效果,基于风险导向审计准则,审计师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到那些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因此,如果审计师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客户,那么审计收费会随着内部控制风险增加而提高。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H1。
H1: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会增加上市公司的合规成本,但是合规成本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形式合规”动机。
(二)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及其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影响
根据COSO以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界定①,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即高管)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核心与关键。有研究认为可以通过调整和优化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与结构(Hoitash等,2009;Johnstone等,2011)[19][6]、CFO的任职资格和变更等(Wang,2010;Li等,2010)[20][5]、削减高管薪酬(Hoistash等,2012;Wang,2010)[21][20]等途径来实现。也有研究认为,全球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与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审计委员会在企业内部控制监控中的角色与问责治理,可以提升审计委员会的监管效率,改善治理水平、重塑良好形象、提高治理效应(刘焱、姚海鑫,2014)[22]。但是作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之中的一项制度安排的高管变更及其权力配置在内部控制缺陷与修复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却鲜有研究。因此如何看待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之间的关系,则有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1. 内部控制缺陷对高管变更的影响。高管人员位居企业科层结构的顶端,在经营决策中拥有重要控制权甚至绝对权力,对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司价值创造、企业竞争力提升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权小锋、吴世农,2010)[23]。因此,高管及其权力配置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效率。就以审计委员会来说,Harris和Raviv(2008)[24]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获得的信息数量与质量受到企业高管权力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审计委员会监管作用的有效发挥;Lisic等(2012)[25]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在公司高管的重压之下,审计委员会大多表现为形式上合规但实质上无效;王守海等(2012)[26]发现,高管对董事会的干预会削弱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监控效力。可见当公司暴露内部控制缺陷尤其是重大缺陷时,高管对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管才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核心要素②。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减少激进性会计行为,及时发现违规舞弊,并且能够惩罚从事如此行为的公司高管,由此,上市公司高管可能会因内部控制缺陷的暴露而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如Goh(2009)[27]发现,与没有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相比,披露重大内控缺陷的公司在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财会专长、人数和董事会独立性等方面得到显著的提高,公司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有效性也得到明显的综合改善。Li等(2010)[5]发现被出具内部控制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CFO的专业任职资格较低;次年发生CFO变更的可能性更高,并且更倾向于聘用资格水平更高的CFO;Wang等(2010)[20]发现在SOX法案之后,企业的CEO变得更加规避风险,CEO的任期更短、离职率也可能更高;Johnstone等(2011)[6]发现公司出现财务重述、内控存在重大缺陷等负面事件后,显著提高了企业高管(如CEO、CFO、审计委员会等)变更的概率。因此,我们预期内部控制缺陷尤其是重大缺陷的披露,意味着上市公司治理层面存在严重问题,上市公司可能会通过变更高管的方式应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引发的资本市场不利影响,改进公司治理,重塑投资者信心。
2. 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影响。已有文献(Brickley等,1999;Khorana,2001;Ting,2013;权小锋等,2009;吴良海等,2013)[28][29][30][31][32]从企业业绩、决策制定、财富效应等方面考察了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更换高管有助于企业业绩改善,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以及并购、研发投资等战略决策也将产生一定影响,而高管变更市场反应的研究结论则莫衷一是。作为一种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极端约束机制,更换高管是否有助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修复?按照内部控制缺陷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主观动机不同,内部控制缺陷存在“无意使然”和“有意操纵”之别,无论是哪一类缺陷,上市公司在发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后,管理层都必须按照内部控制监管的要求,针对已发现缺陷尤其是重大缺陷的类型及其形成原因,在企业内部调动资源对已发现缺陷进行整改,并在下一年度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报告缺陷的整改与修复情况,否则将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如可能连续的获取内部控制非标意见、向外部传递更高的风险信号、面临更严厉的外部监管甚至处罚等③。现有研究也发现,高管变更后,提高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程度,如Li等(2010)[5]发现那些在次年更换高管的公司,审计意见会显著改善;Kryzanowski等(2013)[33]发现新聘任高管的个人资质会显著改善,并且作为信号传递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以前损失的声誉。因此,可以预期继任高管在受到经理人市场的声誉与淘汰机制、资本市场的股价变动、外部审计的审计鉴证以及证监会和交易所监管等方面的多重压力下,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修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综上,提出本文的假设H2。
H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加大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而高管变更则有助于公司修复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以下原则剔除一些样本:(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的合规成本(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数据共8 632个,合规成本(审计费用增加值)数据共有3 026个④,高管变更数据共有9 124个,内部控制修复数据共9 210个。其中内部控制缺陷及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数据来源于深圳迪博数据库,高管变更及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排除极端值影响,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型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工具为Stata11和Excel。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H1与H2,本文分别构建以下检验模型:
ICCCi,t+1=β0+β1ICWi,t+β1Levi,t+β2Roai,t+β3Sizei,t+β4Cfoi,t+β5Jri,t+β6Big10i,t+β7Growthi,t+β8Statei,t+β9Brindi,t+ε模型1
CGImproi,t+1=β0+β1ICWi,t+β2Levi,t+β3Roai,t+β4Sizei,t+β5Growthi,t+β6Statei,t+β7H_10i,t+β8Jri,t+β9Bsizei,t+ε模型2
ICWFixedi,t+1=β0+β1CGImproi,t+1+β2ICWi,t+β3Levi,t+β4Roai,t+β5Sizei,t+β6Growthi,t+β7Lossi,t+β8Opi,t+β9Jri,t+β10Big10i,t+β11Icopi,t+ε模型3
合规成本:陈骏(2014)[9]、Kinney和Shepardson(2011)[18]的研究,合规成本分别以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和审计费用增加额替代。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⑤(记为ICCC1),以上市公司t+1期的销管费用异常变化作为合规成本的代理变量;审计费用增加额(记为ICCC2),以上市公司t+1期的审计费用(扣除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与t期之差的自然对数表示。根据假设1,预期合规成本的系数显著为正。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缺陷修复:两者均来自迪博数据库,前者记为ICW,上市公司t期披露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设为1,否则为0;后者记为ICWFixed,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在后续年度不再出现才视为彻底修复,设为1,否则为0。
高管变更:记为CGImpro,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后的t+1期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更时为1,否则为0。根据假设2,预期高管变更和缺陷修复的系数显著为正。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陈骏,2014;Kinney和Shepardson,2011;王成方,2012;盖地,2013;叶建芳,2012;牟韶红,2014;卢锐,2011)[9][18[34][35][36][37][38],我们还控制了若干其他变量,具体变量名称见表1。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⑧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可知,样本中上市公司年度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ICCC1)的均值为0.002,中位数为0.002,总体而言,2008—201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年度销管费用未出现较大的异常变化。审计费用增加值的自然对数(ICCC2)标准差为1.104,表明其数值变化不大。高管变更(CGImpro)的均值为0.292,表明在2008—2014年期间样本中有29.2%的公司发生了高管变更;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的均值为0.093,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ICWFixed)的均值为0.085,说明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均大部分进行了缺陷修复。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系数矩阵可知,合规成本ICCC1(年度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减少企业年度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合规成本ICCC2(审计费用增加额的自然对数)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内部控制缺陷会导致企业的审计费用增加;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与高管变更CGImpro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很可能导致下一年度企业高管变更;高管变更与企业当年的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高管变更这类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
(二)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研究假设H1的回归结果。表2第1列的回归以合规成本ICCC1(年度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与合规成本ICCC1正相关但不显著;表2第2列的回归以合规成本ICCC2(审计费用增加额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与审计费用增加值显著正相关(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会导致其下一年度合规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导致审计费用的显著增加,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使得审计风險增加,审计师为此收取了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反映上市公司为加强内控建设而投入的直接成本(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并未显著增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控合规成本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形式合规”动机⑧。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H1。
表3第1列给出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ICW)与高管变更(CGImpro)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变更显著正相关(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下一年度更可能发生高管变更;表3第2列提供了高管变更(CGImpro)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ICWFixed)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变更与企业内部控制修复显著正相关(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更换高管有助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修复。根据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要求,内控年审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在下一年是必须进行缺陷修复的,即所谓的“审计信息的市场压力”,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确认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是否确实受到高管变更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来自规范体系的要求。表3第3、4列分别提供了高管变更与高管未变更的分组检验结果,分组检验发现无论在高管变更组还是未变更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修复均与上一年度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中对内部控制评价、审计以及缺陷整改的要求,确实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进一步观察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与披露间的系数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369 6>0.908)⑨,说明高管更换和没有更换,其缺陷修复存在显著差异区别,且高管更换组的缺陷修复明显高于高管未更换组。上述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2。说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迫使上市公司通过高管变更方式改善公司治理,而改进的公司治理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产生积极影响。
五、政府监管不同阶段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尽管我国的内部控制建设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刘启亮等,2011)[39],但是给了企业一定的转换空间,是一个由选择性到强制性渐进发展的过程,如果2008—2011年视为选择性阶段,那么2012年之后便是一个强制性的阶段⑩。因此,我们进一步要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不同时期的内部控制规范的出台以及对企业强制实施力度及威慑力的不同,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信息披露对企业合规成本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甚至缺陷修复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不同阶段影响合规成本的检验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上市公司合规成本影响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表4第1列和第2列中,对比两组检验样本可以发现,在政府强制监管实施后组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ICW)与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ICCC1)之间显著正相关(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在政府强制监管实施前组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ICW)与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ICCC1)之间负相关且不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规范在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强制实施,迫使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为执行监管要求而新增内控方面的投入,即内部控制规范强制实施后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入资源来改善内部控制达到“实质有效”的需求在增加;在表4第3列和第4列中,对比两组检验样本可以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ICW)与审计费用增加值(ICCC2)均显著正相关(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政府强制监管实施后组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审计费用增加值之间的系数更高,近乎是强制监管实施前的两倍(0.342 4>0.175 0),说明内部控制规范在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强制实施,使得审计师面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的风险意识更强。
(二)不同阶段影响高管变更及其缺陷修复的检验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ICW)与高管变更(CGImpro)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规范政府强制实施前影响更大,在政府强制监管实施前组中,无论是回归系数(0.392 6/0.304 6)还是显著性水平(1%/5%)均明显高于政府强制监管实施后,说明来自外部的政府监管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效应,当外部的政府監管力度不够时,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部监管的不足。
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影响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2012年以前,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产生显著正面的影响(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在2012年以后,高管变更与内部控制修复虽然正相关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更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外部监管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因此,本文的研究为改进公司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将企业存在的重要缺陷纳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新进行回归检验,主要研究结果不变;其次,由于非标审计意见和财报差错都是非常严重的内部控制缺陷,因此将这两类样本剔除进行回归,主要研究结果不变;再次,在高管变更数据中将CFO变更也考虑进去,主要研究结果不变。上述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8—2014年的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上市公司下一期的合规成本(上市公司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和审计费用的增加额)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改进(高管变更)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公司进行高管变更后是否会促进企业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以及政府监管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中所起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会导致其下一年度合规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导致审计费用显著增加,但是反映上市公司为加强内控建设而投入的直接成本(年度销管费用异常变化)并未显著增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控合规成本投入更符合“形式合规”动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会迫使上市公司通过高管变更方式改进公司治理,而高管变更则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以不同监管阶段作为衡量政府监管力度差异的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压力的增加迫使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为执行监管要求而增加内控建设方面的投入,且公司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部监管的不足。
本文的启示在于,我国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尽管出现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能够进行整改,但是这种整改更多的是满足“监管需求”和迫于“外在压力”,尚未真正形成源于内部管理需要和自律监管的环境和意识。监管压力、强制推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企业自我修炼和觉醒,内部控制就很难达到预期的制度安排目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内部控制建设进程中,企业高管关于内部控制的自觉、自信和自省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内部控制建设的内在禀赋,而政府监管作为外在的推力,也是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力量,没有政府监管的压力,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力度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的研究为如何改善公司治理、修复内部控制缺陷提供借鉴,丰富了关于内部控制缺陷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加强内部控制政府监管提供了重要依据。
注释:
①内部控制是一个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②SOX法案302条款要求,上市公司CEO、CFO负责建立和维持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保证CEO、CFO能够全面了解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所有重大信息,并评估内控体系是否有效可行。
③2013年和2014年,大有能源(600403)连续两年皆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其原因在于尽管发现重大缺陷后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但由于整改不力,同样的内控重大缺陷在第二年再次出现。
④本文采用扣除內控审计后的审计费用增加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多数公司审计费用前后两年没有变化,在剔除的样本中,有862个是审计费用减少的样本,有4 453个样本是审计费用未发生改变的样本。
⑤陈骏(2014)的研究中以上市公司累计销管费用异常变化作为合规成本的代理变量,检验上市公司在内控监管实施前后是否因内控监管而增加了额外的企业遵循成本。而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是否迫使企业新增投入,导致该公司下一年度合规成本的显著增加。而年度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恰能衡量的是企业当年为执行监管要求的新增投入,故本文选择了此指标。
⑥企业当年出现证券会处罚、财报差错更正、获得非标审计意见情况之一时,也视为企业当年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⑦限于篇幅,没有列示具体的过程和数据,资料备索。
⑧这一结果与我国财政部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和2013年开展的相关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调查显示,企业内各级人员在内控建设中仅满足于“合规”要求,企业管理水平未见显著转变。
⑨我们对上述两组样本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Chi2=5.10,Prob>Chi2=0.023 9(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⑩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出台、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颁布》以及证监会明确制定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时间表——自2012年起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按照制度变迁理论,自愿性(选择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变迁的主体、方式、路径、成本效益等方面都存在区别。本文根据我国内部控制实施的不同阶段进一步深化研究,有助于发现不同监管阶段的差异,从而为更好地完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提供增量信息。
参考文献:
[1]Rice S C,Weber D P.How Effective Is Internal Control Reporting under SOX 404· Determinants of the Non-Disclosure of Existing Material Weakness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2,50(3).
[2]Hambrick D C,Mason P A. 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
[3]程小可,郑立东,钟凯.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研究综述[J].科学决策,2013,(3).
[4]Hambrick D C. Upper echelon theory:an updat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2).
[5]Li,C.,L.Sun,and M.Ettredge. Financial Executive Qualifications,Financial Executive Turnover,and Adverse SOX 404 Opin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
[6]Johnstone,K.,Chan Li,and K. H.Rupley. Chan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Revel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Material Weaknesses and Their Subsequent Remedi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1,(28).
[7]Hall,L.A.,Gaetanos,C.Treatment of Section 404 Compliance Costs[J].The CPA Journal,2006 ,76(3).
[8]Leuz C.,Triantis A.,Wang T.Y.,Why do Firms Go Dark? Cause and EconomicConsequences of Voluntary Deregistra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45(2-3).
[9]陈骏.内部控制监管、遵循成本与监管效果——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经验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6):75-84.
[10]Ahmed A.S.,McAnally M.L.,Rasmussen S.,Weaver C.D.How Costly is the SarbanesOxley Act?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the Act on Corporate Porfitability[J].Journal of CorporateFinance,2010,16(3).
[11]Alexander C.R.,Scoot W.Bauguess.,G Bernile,Y-H Alex Lee,J.Marietta-Westberg.Economic effects of SOX Section 404 compliance:A corporate inside perspective[J].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3,56(2-3).
[12]Ashbaugh-Skaife,H.,Collins,D.,Kinney,W.,LaFond,R.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9,47(1).
[13]Raghunandan K,Rama D. SOX Section 404 Material Weakness Disclosures and Audit Fees[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6,25(1):99-114.
[14]Hogan,ChrisE,and Michael S.Wilkins,“Evidence on the Audit Risk Model:Do Auditor Increase Audit Fees in the Presence of Intemal Control Deficienei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8,25(1).
[15]Hoitash R,Hoitash U,Bedard J C.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audit pricing under the Sarbanes-Oxley act[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8,27(1).
[16]張敏,朱小平.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与审计定价关系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J].经济管理,2010,(9).
[17]李越冬,张冬,刘伟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产权性质与审计定价[J].审计研究,2014,(2).
[18]Kinney,W.R,M L Shepardson."Do Control Effectiveness Disclosures Require SOX404(b).Internal Control Audit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Small U.S.Public Companies,"[J].Journal of Accountancy,2011.
[19]Hoitash,U.,R.Hoitash,and J.C.Bedard.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A Comparison of Regulatory Gegime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
[20]Wang,X. Increase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Decisions:Evidence from 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0,(48).
[21]Hoitash.R,Hoitash U., K. M., Johnstone. Internal Control Material Weaknesses and CFOCompensation[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2,29(3).
[22]刘焱,姚海鑫.高管权力、审计委员会专业性与内部控制缺陷[J].南开管理评论,2014,(2).
[23]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
[24]Harris,Milton,and Artor,Raviv. A Theory of Board Control and Size[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8.
[25]Lisic,L.L;Neal,T.L;Zhang,I;Zhang,Y.CEO Power,Internal Control Qualigy and 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in Substance Versus in For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asearch,2012,33(3).
[26]王守海,李云.管理层干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J].审计研究,2012,(4).
[27]Goh B W.Audit Committees,Boards of Directors,and Remediation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9,26(2).
[28]Brickley J A,Linck J S,Coles J L.What happens to CEOs after they retire? New evidence on career concerns,horizon problems,and CEO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52(3).
[29]Khorana A.Performance Changes following Top Management Turnover:Evidence from Open-End Mutual Funds[J].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1,36(3).
[30]Ting H I.CEO turnover and shareholder wealth:Evidence from CEO power in Taiwan[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12).
[31]權小峰,吴世农.长期任职董事长离职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管理,2009,(8).
[32]吴良海,谢志华,周可跃.公司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3]Kryzanowski L.,Ying Zhang,Financial restatements and Sarbanes-Oxley:Impact onCanadian from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urnover[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3,21(Jun).
[34]王成方,叶若慧,于富生.审计意见、政治关联与高管变更[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5).
[35]盖地,盛常艳.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3).
[36]叶建芳,李丹蒙,章斌颖.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2,(6).
[37]牟韶红,李启航,于林平.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审计费用——基于2009—2012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4).
[38]卢锐,柳建华,许宁.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J].会计研究,2011,(10).
[39]刘启亮,刘晶莹,谈丽华,张雅曼.IFRS的强制趋同、盈余动机与应计及真实盈余操纵[J].财会通讯(综合版),2011,(5).